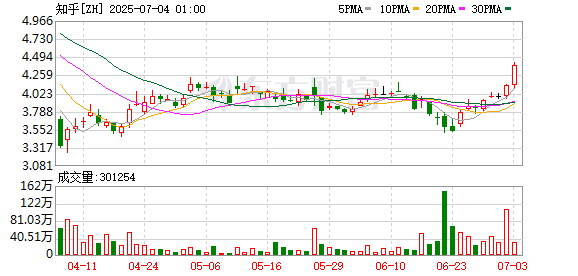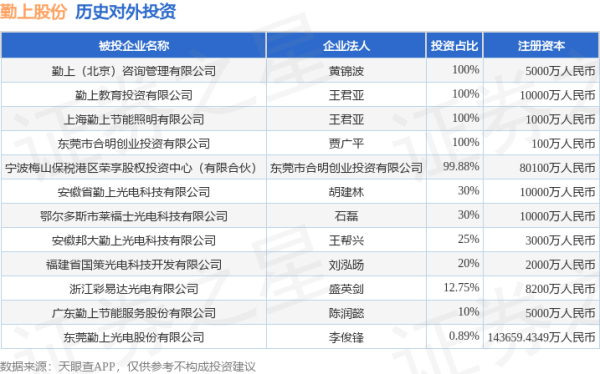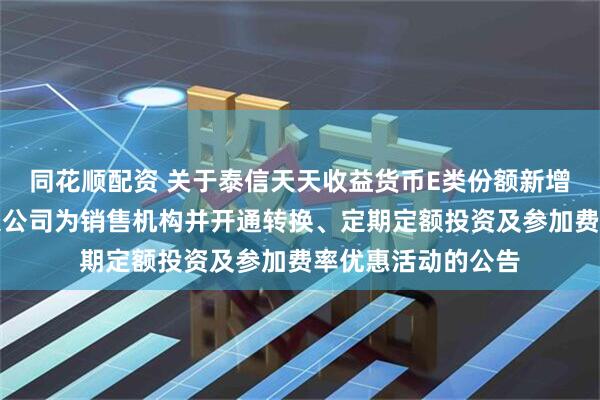紫禁城的深夜牛跟投,一位少年皇帝,在帷幔之中静静凝望眼前跪地不起的老将。
那是鳌拜,这位权倾朝野却最终身陷囹圄的大清权臣,用半生换来的“勋章”。
这究竟是怎样一场帝王与权臣之间的博弈?
又为何,明明罪责难赦,康熙却最终放过了他?
少年将军清初岁月,满洲铁骑横扫辽东平原,在这支锐不可当的劲旅中,有一位少年将军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功劳簿上。
他不是皇亲国戚,也并非出身显赫,而是凭着血与汗、一把刀、一杆枪,一步步从战场杀出了一条血路,就是瓜尔佳·鳌拜,在战火中被称为“巴图鲁”的男人。
展开剩余90%鳌拜所在家族系瓜尔佳氏,隶属镶黄旗,祖辈世代为兵,少年时代,他便随皇太极麾下征战四方,从辽东草原到大明边疆,每一场血战都是他成名的阶梯。
让鳌拜初露锋芒的,莫过于1637年皮岛之战,彼时,明军退守皮岛,八旗军以骑兵见长,面对这座孤悬海中的堡垒显得束手无策,皇太极亲自督战,数次命人强攻无果。
就在众将心生犹豫之时,年纪尚轻的鳌拜挺身而出,带着一支小队绕过主攻方向,从海岸边破浪而行,趁夜幕掩护,摸索着接近敌营,在敌人尚未察觉时迅速爬上海崖。
那一刻,皮岛的战局被彻底改写,鳌拜成了第一位踏上皮岛的清军将士,力斩明军百余,战后,皇太极亲赐“巴图鲁”称号,并封其为三等男爵。
从皮岛归来后,鳌拜又陆续参与了松锦会战、锦州之战等重要战役,每一次战斗都冲锋在前,哪怕身陷重围也绝不退缩,营中兄弟都说他是铜皮铁骨,死神都不肯收他。
清军入关之后,鳌拜马不停蹄地参与剿灭南方起义军的战役,面对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,他不只勇猛,更善于率兵突袭,屡次扭转败局。
相传,他每次出战都披坚执锐、亲自督战,手中长刀斑驳如铁锈,那是敌人鲜血浸染留下的痕迹,也是他功勋赫赫的象征。
不仅如此,鳌拜对于皇太极的忠诚也在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,皇太极常言。
“八旗铁骑虽强,唯鳌拜不惧死。”
正因如此,鳌拜逐渐成为皇太极身边的铁杆将领之一,不仅在军事上倚重,在政治斗争中也多次受命,显示出极大的信任。
皇太极猝然驾崩后,皇位继承问题骤然浮出水面,豪格与多尔衮之争暗潮汹涌,此时的鳌拜已是统兵在手、功勋卓著的实权将军,他没有立刻站队,最终推举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。
这一政治决定,在当时无疑是一次冒险之举,但也体现出鳌拜对皇太极一脉的忠诚,此举虽得罪了多尔衮,却坚定了清廷的皇权传承,为大清江山稳住了根基。
权力博弈当年,顺治帝初登基时年仅六岁,幼主临朝、权臣当道,本是王朝危机四伏的阶段,然而,此时的朝堂却因一位武将的存在而显得格外稳固。
在顺治还是皇子时,便常听皇太极与诸将谈及“瓜尔佳家的小鳌”,是一个哪怕箭穿胸膛也要挺身挥刀、冲锋在前的猛士,正是这“忠烈之骨”让顺治即位之初便对鳌拜格外倚重。
好在,鳌拜并未辜负这份信任,对顺治帝恪尽职守、忠心耿耿,即便在多尔衮掌权时期遭受多方排挤、任意削权,他也未曾动摇对大清的忠诚。
直到多尔衮意外身亡,顺治帝亲政,鳌拜也随之迎来仕途上的大翻盘,不仅重新掌兵,还被任命为“议政大臣”,跻身朝堂高位,逐步收回过往被削的权力。
不仅如此,顺治还曾亲自探望病中的鳌拜,这在清代皇帝对臣下的礼数中极为罕见,朝中上下无不感叹,这位老臣在皇帝心中已非常人所比。
就在顺治去世、康熙帝年幼登基后,鳌拜的影响力变得愈发膨胀,其他三位辅臣各有隐忧,索尼年老避事、苏克萨哈根基不稳、遏必隆则多随波逐流,朝堂之上几近鳌拜一人主事。
他的人马遍布六部要职,许多奏章未经皇帝御览,便先被他批阅一遍,连康熙帝的近侍中也有他安插的眼线。
此时的鳌拜已然忘了自己曾是那个在战场上跪谢皇恩的将士,在权力的高位上久坐不下,甚至产生了与皇帝分庭抗礼的念头。
他的府邸门前车马不息,百官趋之若鹜,俨然已成“摄政王”般的存在,满朝文武无人不知鳌拜之权重,也无人不敢与其正面交锋。
康熙尚年幼,深知目前无法硬碰这位“老虎大臣”,鳌拜此时丝毫没有察觉风向微妙,仍以为自己高高在上、皇恩如昔,不知天已渐变,杀机已伏。
康熙毕竟不是寻常皇子,自幼在孝庄太后熏陶下长大,早熟机敏,冷静而隐忍,他明白,硬碰鳌拜无异于以卵击石,唯有智取,方能一招制敌。
他开始假装沉迷玩乐,大量召募京中武艺出众的少年,日夜在宫中表演布库,一种满族摔跤游戏,宫廷中人皆以为皇帝心志尚幼,沉溺儿戏,鳌拜更是冷眼旁观,甚至私下讥讽。
“小皇帝不过一群猴子取乐。”
此外牛跟投,康熙还在一步步剥离鳌拜的外围力量,借“升迁调任”之名,将鳌拜亲信逐出权要之地,又让太医院例行检查,将数名亲卫调离宫禁。
宫中渐归康熙掌控,鳌拜却全然不察,反倒以为小皇帝无心朝政,更加肆无忌惮,时机终于在康熙十六岁这一年到来。
一日,康熙下旨召鳌拜入宫,表面上是“商议朝政重务”,实则是请君入瓮,鳌拜大摇大摆地步入乾清宫,没有佩戴随身兵器,带着一种“无人敢动我”的气势。
乾清宫内,布库少年早已埋伏妥当,康熙坐在龙案之后,平静地注视鳌拜跨入殿中,那一刻,时光仿佛凝滞,年少皇帝的眼神如寒刃般锐利。
“动手!”
尚未回神,鳌拜便被数名少年猛扑在地,他力大无穷,怒吼之下竟挣断绳索,一度试图翻身而起,但那些少年如壁垒般死死压住他,七手八脚将其制服。
康熙没有立刻宣判,而是当众斥责鳌拜种种罪行,细数他这些年如何目中无君、草菅人命、侵夺国权,言语之中再无半点犹豫,随后命人彻查鳌拜府邸,连夜封禁鳌拜党羽之所。
那一夜,北京城风声鹤唳,鳌拜的旧部如鸟兽散,唯恐被株连,数日之内,康熙雷霆手段,迅速肃清鳌拜余党,长久以来“鳌拜治朝”的格局轰然崩塌。
侥幸免死鳌拜沦为阶下囚后,这个曾经权倾朝野的巨人,变得腰背佝偻、步履沉重,走在自己人生的末路,他很清楚,康熙必定会给他从重定罪。
一日,朝臣聚首之际,康熙面无表情地宣告。
“众卿可列鳌拜罪状,按律议处。”
言下之意,就是要鳌拜死,群臣激动溢于言表,他们这些年被压抑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出口,有人拍案叫好,有人甚至喜极而泣。
鳌拜的命,如今就挂在康熙一句话上,可就在行刑前的那个黄昏,鳌拜却提出了一个请求,他想见皇上一面。
“老臣,有话要说给皇上听。”
康熙沉吟许久,终究还是点头同意了,他想知道,这位他亲手擒下的巨擘,死前到底还有什么要说。
当鳌拜被带到殿前时,天色已暗、宫灯摇曳,康熙静坐在案后,目光冷冽地望着这位昔日的辅政大臣。
鳌拜没有下跪,只是缓缓抬起头,那双曾经锐利的虎目如今早已浑浊,望着康熙却没有立刻说话,突然扯断囚衣衣襟,将自己的上身裸露于殿前。
殿内寂静如死,康熙的目光顿时定住。
鳌拜早已不是昔日战场上威风凛凛的模样,而是一具布满伤痕的身躯,纵横交错的刀痕、枪刺、烧灼之痕布满胸背,有的蜿蜒如蚯蚓,有的深陷如沟渠。
这不是一副囚犯的身体,而是一部活生生的战争史书。
康熙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直视鳌拜,亦从未真正意识到,这个令他如芒在背的敌人,曾在枪林弹雨中为这片江山出生入死。
“皇上,这些,不是为了我自己,是为了大清,老臣从十四岁起随军,不求富贵,不求长寿,只求对得起皇太极、对得起顺治、对得起大清。”
康熙原本冷峻的脸庞终于动容了,想起了父皇口中反复提及的那位“战将鳌拜”,也想起自己幼时曾在墙角偷偷听见的议政大臣间的低语。
“皇上……老臣知罪,也无颜再求活命,但臣敢发誓,臣未曾谋反,未曾负皇上分毫,若皇上不信便赐一死,若尚存念旧之情便饶老臣一命,永不复朝堂。”
康熙闭上眼,心中翻涌,他曾在梦中数次怒斥鳌拜,想象着那张高高在上的面孔落地后众臣欢呼的场景,不止一次告诉自己。
“不杀鳌拜,便无皇权。”
可就在此刻,那满身疤痕,仿佛是一双只会流血的手拽住他的衣襟,那不是鳌拜一个人的疤,是三朝铁血历史的遗痕,是父皇留给他的最沉重的信物。
沉默许久,康熙缓缓站起身,走下龙阶,站在鳌拜面前,目光与他对视,那一刻,帝王的眼中泛起一丝水光。
“念尔军功,忠心曾显,虽罪当诛,朕不忍加杀,自今日起,褫夺一切官职,收押天牢,终身囚禁,不得复出。”
“谢皇上。”
鳌拜终究没有死在皇帝手中,而是带着满身疤痕,缓步退出了权力的舞台,此后,他被囚禁于北镇天牢,再未踏出一步。
康熙八年,他静静死在囹圄之中,没有成为忠臣楷模,也没沦为权奸之首,而是留在历史的夹缝中,成为一段难以评说的沉重记忆。
康熙的一滴泪牛跟投,换回了鳌拜的一条命,也划下了那个权臣时代的终止符。
发布于:山东省龙辉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